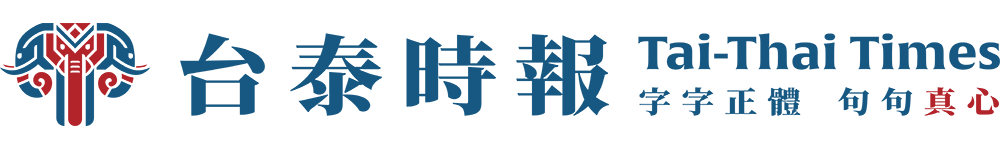(台泰時報曼谷電)在泰國社會,警察向來被視為是高度制度化、也最貼近國家權力核心的角色之一。對多數民眾而言,警察體系既象徵秩序與強制力,也長期承載著關於權力運作、貪腐結構與責任邊界的複雜爭議。在這樣的集體認知下,警察往往被視為體制的執行者,而非質疑體制的人。
然而,考察泰國近代政治與警政史中,確實仍存在著少數難以被歸類的例外。他們即便不再身居高位,卻始終無法被忽視;他們的存在,本身即是一種對體制的提問。出身警界、曾擔任皇家泰國警察總監的退役警察上將 Sereepisuth Temeeyaves(泰文:เสรีพิศุทธ์ เตมียเวส),正是其中最難被放入既有政治框架的一位。
卸下制服後,他沒有選擇進入企業體系、擔任顧問,或逐步淡出公共視野,而是反向走進政治場域,成為泰國體制內少數長期對權力結構提出質疑的政治人物之一。對台灣讀者而言,他的經歷不僅是一段泰國政治的個人敘事,更是一名長年站在執法核心的人,如何在制度邊界上作出選擇的現實樣本。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,透過台灣會館副主席王載麟的引介,《台泰時報》得以就警政治理、制度改革與政治選擇等議題,對這位長期站在體制邊界的人物,進行一次完整而深入的訪談。以下就是這次專訪的整理:
看見「國家失敗」的那一刻:走出警察體制的轉折
談及從警界轉入政治的起點,Sereepisuth 並未以個人榮辱或職涯規劃作答,而是反覆提到一個關鍵時刻,「第一次清楚意識到國家正在失敗」。
他坦言,警察體系能處理的,往往只是問題的結果,而非根源。即便身處體制高層,他愈發清楚,許多社會亂象並非執法鬆散所致,而是政治決策失能、制度被利益結構綁架的後果。當警察體系無法再承擔改革期待,他選擇離開原本最熟悉的位置,嘗試從政治層級回應問題。
在旁人看來,退休後轉入政治並非多數警界前輩的選項,但他對此看得直接:「如果什麼都不做,反而會更快耗盡。」對他而言,持續行動既是一種責任,也是一種生命狀態。

泰國參選的現實:沒有黨機器,就沒有戰場
在正式成立政黨前,Sereepisuth 曾以個人名義投入大型地方選舉。這段經歷,讓他對泰國選舉政治有了更殘酷的認識。他直言,沒有政黨機器與資金支撐的候選人,只能逐區拜票、逐點說服,一天往往只能跑一個地方;相對之下,大型政黨透過既有系統,一天便能鋪排數十個選區的資源與人力。最終,他在該場選舉中僅名列第三,前兩名皆由泰國主要政黨拿下。這場敗選,並未讓他退卻,反而促使他確信:若不建立組織力量,改革將永遠停留在口號層次。
2019 年,Sereepisuth 正式成立政黨並投入國會選舉,首次參選即取得十席立法席次。在泰國多黨政治結構中,這樣的結果被視為相當亮眼,也讓他成為組閣過程中的關鍵少數。多方勢力隨即展開接觸,希望拉攏他加入執政陣營。談判桌上,出現了包括副總理職位、警政體系主責權限,乃至高額政治資源的條件。但他最終選擇全數拒絕。理由並不複雜。他認為當時的政權並非透過正當民主程序產生,若在此情況下進入體制核心,等同替不正當權力背書。
拒絕加入政府後,Sereepisuth 迅速成為國會中最具對抗性的在野監督者之一。他的作風簡單而直接,只要發現違法,就提告,不論對象是部會首長或前後任總理。這樣的行事風格,為他累積支持者的同時,也讓他付出政治孤立的代價。隨著選制在 2023 年調整、投票制度更趨複雜,選後結果歷經長時間反覆計算與爭議,他所屬政黨的國會席次最終大幅縮減至僅剩一席。地方支持者與候選人也在現實考量下陸續流失,原本遍布各地的布局,縮減至約二十一個選區。
改革作為畢生志業
即便政治現實屢屢碰壁,Sereepisuth 對改革的排序始終明確。他將警察改革列為第一優先。原因不是抽象理想,而是可行性—,警政系統是他最熟悉的領域,只要制度與命令到位,就能立即產生改變。他認為,若警察體系能回到專業與紀律軌道,詐騙、貪腐與基層治安問題不應如此失控。
第二順位是教育。他主張國家至少必須確實落實十二年教育責任,同時發展多元職業教育,而非只以大學升學作為唯一出口。他也直言,教育資源長期遭政治人物挪用,從學生的午餐、牛奶到校園運動空間,品質全面下滑。
第三是醫療。基層民眾凌晨排隊看診、一整天耗在醫院的現象,在他看來不該成為常態。他主張將醫療設備與專業人力下放至各省區,避免重病患者被迫全部湧入曼谷。
談到台灣政治,Sereepisuth 認為兩國文化相近,但關鍵差異在於制度韌性。他指出,台灣即使政治對立激烈,仍能在體制內修正、前進;相對之下,泰國政治長期被金錢與利益設計成「通行證」,選舉幾乎等同資本競賽。
他不諱言,要打破這種結構,必須從國會法制面動手,但在現實條件下,大黨並無誘因推動真正限制自身的改革。

仍然站在場內的人
在多數人選擇沉默、妥協,或逐步退場的政治環境中,Sereepisuth 仍選擇留在場內。他並不對勝敗作出承諾,也不預設改革必然成功,而是反覆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:當制度出現偏差時,是否仍有人願意承認問題的存在,並為指出問題承擔後果。
這樣的選擇,未必帶來權力,也未必換得掌聲,甚至可能導向孤立與失敗;但正是在這些不確定性之中,一個政治體制是否仍保有自我修正的可能,才得以被檢驗。對他而言,政治從來不是必勝的算計,而是一場漫長、耗損、卻不能缺席的制度之戰。留下來的人,不一定改變歷史,卻讓制度仍保有被質問的空間。